會放上這篇,主要是今晚聽了大甲媽祖相關主題的演講,心有所感。至於有什麼感,改天再告訴你們囉。
頭城搶孤的社會互動與空間擴張-從儀式到民俗[1]
游牧笛[2]
摘 要
搶孤為閩南文化中鬼厲信仰的重要宗教儀式,其中透過搶孤活動的舉行,從而發展出來的木工技藝、糊紙藝術與宗教文化均受到學術界、藝文界的重視;除此之外,搶孤更能夠反映出當時的民風、地方經濟、村里間的連繫與對抗等社會結構,對於瞭解地方的發展具有其一定的指標性。經過長達半世紀的停辦後,近年搶孤在政府與地方有力人士的推波助瀾,逐漸加入更多現代元素,除了在保留傳統文化上盡一份心力,更企圖將地方特色行銷於外,搶孤從宗教儀式轉變成為了充滿經濟行為、行銷手法的民俗活動,而與社會的互動模式也有所改變。
本文利用搶孤活動對於社會文化發展歷程的指標性,探討地方宗教儀式如何演變成為一普通民俗活動,並逐漸走出地方,並探討其發展策略與社會互動空間的演變。最後提出頭城搶孤雖然因經費問題須不斷擴張其社會互動範圍,並迎合大眾之喜好,但更因專注於保存其原有的文化、社會與宗教內涵,使之在華麗外表之下也能兼顧其做為「無形文化資產」的重要意義。
關鍵字:頭城、搶孤、民俗活動、宗教儀式、文化資產
壹、研究緣起
臺灣做為一個擁有多元文化的社會,近年來在各地大力推動文化觀光之下,各種不同具有地方性的文化節慶一一被呈現於世人面前。宜蘭縣頭城鎮做為「開蘭第一城」,具有相當特殊的宗教儀式-搶孤,其背後的人文背景意義深遠,且舉辦搶孤對於現代頭城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皆有其影響力。近年來在全球化思潮的影響下,頭城也加入了行銷的概念,於搶孤活動中增加了許多普羅大眾所喜愛的元素,如體育競爭、煙火秀等,力求向外地宣傳其鄉土特色,期望能帶動地方知名度與經濟活動,已非早年純粹的庄頭共同祭祀活動。本文將利用頭城搶孤背後所隱含的社會、歷史、文化之內涵,加上現代化民俗活動的行銷概念,探討下列事項:
1. 頭城搶孤的舉辦與地方社會的互動關係為何?
2. 頭城搶孤在不同時代背景之下,其影響的範圍與社會互動空間擴張的脈絡為何?
3. 頭城搶孤未來發展可行的走向與應注意的事項為何?
貳、頭城搶孤之文化意涵
搶孤,是兩百多年以來在流傳於閩南文化中的宗教儀式,現代臺灣仍能夠於宜蘭縣頭城鎮、屏東縣恆春鎮兩地可見到搶孤的舉辦,其中頭城搶孤規模宏大、競爭激烈,是近年來最受矚目的地方文化活動之一。縱觀頭城搶孤活動之舉辦與發展歷程,其間牽涉層面極為廣泛,橫跨歷史文化、宗教傳統與社會結構等面向。
一、 歷史文化
頭城搶孤之所以能如此盛大,與蘭陽平原的開墾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漢人與居住於蘭陽平原的噶瑪蘭族人,早在十八世紀便有貿易活動的進行,然而少數投機之人欺負噶瑪蘭族人不識漢字等,使得雙方互動漸生嫌隙,並發生數起漢人被殺害的事件,如乾隆三十三年(1773)林漢生入墾蘭陽失敗被殺、嘉慶元年(1796)吳沙首次入墾今日烏石港南地區遭抵抗導致多人戰死等;除噶瑪蘭族之外,頭城附近山區的泰雅族人也經常出草,殺害於蘭陽平原開墾之漢人。(林正芳,2002)[3]
在漢人勢力逐漸穩固之後,由於移入噶瑪蘭地區分別有漳、泉、粵等不同原鄉之族群,遂發生了數次分類械鬥,分別為嘉慶四、五年(1799~1800)的粵、泉械鬥,嘉慶十一年(1806)粵、泉州人聯合番人攻擊漳州人等;噶瑪蘭設治後,發生於頭圍街的械鬥則為同治十三年(1874)的西皮、福祿之爭為最。(林正芳,2002)[4]
從早期拓墾時的漢、番衝突到後來的分類械鬥,頭城地區經常有許多無名死者,或無子嗣、或流落荒郊,於民間信仰中成為「厲鬼」,人多敬畏之,因此建立許多有應公廟、金斗公廟等,並加以祭祀,以祈求平安,因此,頭城每年於中元時的搶孤活動也最為盛大,且歷史悠久,並逐漸成為宜蘭地區代表性的文化資產。
二、 宗教傳統
搶孤為鬼厲信仰中的一部份,是中元普渡最後、最盛大的儀式。中元普渡受到各種宗教文化的影響,如官倡之儒家思想、道教與佛教教義均在普渡儀式中被抄襲與應用(黃進仕,2000)[5]。儒家思想為漢人社會的主要生活依歸,傳統上對鬼神具有「仁厚」與「畏懼」的雙重心理,在《春秋》中描述道「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之民間習俗,漢人社會對於孤魂野鬼均加以謹慎祭祀;臺灣地區為移民社會,拓墾過程中死難者眾,且多無子嗣祭祀之,因而在漢人社會有許多藉由官方所設置之「厲壇」,做為祭祀之用,而民間也普遍立祠祭祀,形成儒家文化下的「祭厲傳統」。
佛、道二教均融合前述傳統儒家思想中的「慎終追遠」,對於先人之追思均有一套儀式。佛教最具體展現於「盂蘭盆會」之儀式,盂蘭盆為梵文音譯,意為「在缽中放置供品施供祖先,以解救祖先免除地獄倒懸之苦」[6],契合儒家孝道思想,因而廣為官方與大眾接受,並於農曆七月十五日舉行儀式(吳明遠,2001)。道教則於三官大帝之信仰中呈現,農曆七月十五日被定為中元日,為地官降至凡間考核人間禍福之日,在唐代皇室尊崇道教先祖老子的情形下,盂蘭盆會的施行逐漸受到抑制,至宋代則發展出「水陸法會」,傳統中國中元祭典科儀的「佛、道融合」逐漸成形[7]。
上述三家對於孤魂野鬼之祭祀行為,具體展現於搶孤儀式中,以道教科儀最為明顯,例如有極為華麗的主普壇(圖1)、道士誦經作法(圖2)等,然而部分人士進行普渡儀式時,受到佛教之影響,所準備之供品為純素。而在搶孤時立飯棚、孤棚等,乃是基於儒家人道精神,將祭品施捨予窮困者或社會弱勢者的手法,因此我們可以將整個搶孤儀式的進行,視為是三教部分教義的互相結合(黃進仕,2000)[8]。


圖1 頭城搶孤之主普壇 圖2 道士帶領參賽者繞行搶孤會場
(筆者拍攝,2009.09.18) (筆者拍攝,2009.09.18)
三、 社會結構
游謙(1995)在討論搶孤的歷史演變時,將之以形式分類為「門口搶孤」與「集體搶孤」兩大模式[9],門口搶孤為清代早期,家家戶戶於門口擺放祭品,並於家門口搶孤的形式;而集體搶孤則是將祭品統一送至大型孤棚,由所有人一起搶奪的形式。不同形式的搶孤活動代表不同時期的社會結構。清道光年間的任職噶瑪蘭通判的烏芳竹於〈蘭城中元〉一詩後有註解寫道:
蘭每年七月十五夜,火燭天,笙歌喧市,沿溪放燄,家家門首各搭
房臺,排列供果,無賴之徒相奪食,名為搶孤。[10]
可知道光年間的搶孤活動是屬於門口搶孤的形式,雖然究竟何時由門口搶孤轉型成為集體搶孤,已經不可考,但以社會安全而言,一群無賴聚集在某處爭奪祭品,總是比在自家門口爭搶,來的安全與易於管理。我們可以從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牧師於回憶錄中所描述的段落得知,早年搶孤時盛大、刺激與野蠻的狀況:
我見過最嘈雜和可厭的場面,便是「七月祭」,七月為供祭所有死
靈的時節,也是大家歡樂興奮的時候。……。在這圓錐形竹架上,從底
部到頂上,處處掛滿了巨量的食物,以供奉死靈;包括熟鴨、生鴨、小
雞、豬肉、魚、餅、青果、香蕉、鳳梨,及四季的各種山珍海味,……。
……;未幾,即見一大群成千成萬的乞丐、遊民、賭徒及各種亡命
之徒等非死靈,……,不耐煩的等待著輪到他們的「牙祭」。……,這
地方已變成一個瘋人院;……,演成一幕粗野的場面。每一個人都帶走
許多東西,……,手裡便緊緊提著搶來的食物。但外圍的人尚未搶得東
西,乃轉向這些攜有食物的人襲擊。……目前這種「七月祭」的野蠻行
為,已完全廢止,這是由於開明的巡撫劉銘傳之改革所致。
馬偕(1895),《宣教回憶錄》[11]
參、頭城搶孤活動的演進
搶孤活動在兩百餘年的發展過程中,其形式略有改變,除前章所述之從門口搶孤演進至集體搶孤,為第一階段的搶孤活動。然而在清代地方官禁止、秩序考量下,至日治後期有了第二次的轉變,也就是由集體搶孤轉變為「選手搶孤」[15],其參與搶孤的成員,已由四方貧困之地的遊民、乞丐、賭徒及各種亡命之徒,轉變成為擅長攀爬的運動健將參加,從前的暴亂場面、被人群踩死等狀況已經不復見了。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時的搶孤活動中,孤棚旁的飯棚依然由批鹽、挑貨等社會底層的人士搶奪,因此仍能在飯棚搶孤中看到早期集體搶孤的狀況。此外,今日所熟悉之搶順風旗也加入了搶孤儀式,搶奪貢品與順風旗同時成為了重要的元素。日治後期以前,可稱為「儀式期」,搶孤舉辦之目的在於進行宗教儀式,藉以祈求來年的風調雨順。
二次大戰期間因民生物資缺乏,頭城搶孤停辦數年,日本戰敗後,首任頭城鄉長盧贊祥提倡下,於民國三十四年復辦,然而在復辦的次年即發生嚴重意外,第三任鎮長黃竹旺於是廢止頭城搶孤的舉辦,盧贊祥更直接將孤柱全數賣至外地[16],直接根絕頭城搶孤所需的物品;另有一說則指國民政府認為搶孤活動過於迷信、暴力,不利於統治,遂指示地方政府予以禁止[17]。不論原因為何,都使得頭城搶孤進入了將長達半世紀的「衰弱期」。
在停辦了四十二年之後,頭城鎮於民國八十年在宜蘭縣長游錫堃支持下復辦,然而因停辦近半世紀,許多工法、祭儀已無法完全掌握;參與的人對於儀式已不再重視,轉而單獨重視搶奪順風旗;同時,社會學者瞿海源(1992)認為傳統的搶孤是「嚇鬼、騙鬼和利用鬼」,而公開主張恢復此活動時應釐清目標、妥善規劃,完全以觀光活動或民俗體育活動的形式來處理,不應任意與宗教牽連或胡亂附會[18]。因此頭城搶孤不再被視為儀式性極強的宗教活動,而逐漸成為了僅具地方性的「民俗活動」,因此將復辦之後的搶孤稱為「民俗期」搶孤。
 |
頭城搶孤由宗教科儀轉變成為民俗競技活動,其中不可忽略的理由即長達半世紀的衰弱期,加上社經背景的轉變,致使原本應負有社會重任的搶孤活動,喪失其既有的文化根源,在政府與地方單位勉力重現之時,在「被重視才有經費」、「破除迷信」等社會環境之下,搶孤活動不得不朝著民俗化、競賽化,甚至綜藝化、商業化發展,最終成為今日所見之頭城搶孤活動-「一個以獎金吸引參賽者、以煙火吸引觀眾、以廣告和園遊會吸引遊客的年度地方民俗文化盛事」(圖4、圖5)。


圖4 為吸引人潮而設計的煙火秀 圖5 搶孤會場旁的園遊會一隅
(筆者拍攝,2009.09.18) (筆者拍攝,2009.09.18)
肆、社會關係的空間改變
頭城搶孤經過兩百餘年來的演變,歷經儀式期、衰弱期與民俗期,與社會的互動也大幅的改變。在儀式期時,無論是門口搶孤、集體搶孤都是反映出當地社會的現況,如飢貧、財富差距、地方特產以及庄頭凝聚力等表徵,然而此時的搶孤僅大致與頭圍街(今頭城鎮一帶)周圍互動;至選手搶孤時期,除頭圍街周圍外,又有其他街庄加入聯合祭祀的行列,至此總計有頭圍街(約為今日頭城鎮城北、城東、城西、城南、新建里)、拔雅林庄(約為武營、拔雅里)、福成庄(約為福成里)、金面庄(約為金面、金盈里)、二圍庄(約為二城里)、港澳庄(約為港口里、外澳里)、大罟坑庄(約為大坑里)、頂埔庄(約為頂埔里)、下埔庄(約為下埔里)、三抱竹庄(約為竹安里)、中崙庄(約為中崙里)和白石腳庄(約為今日礁溪鄉白雲村、玉石村)在祭祀範圍之內,顯然,日治晚期的頭城搶孤與社會互動的範圍,由家戶、頭圍街單一街庄擴張至烏石港、礁溪、竹安的三角形內各街庄。
各街庄間並不僅有合作,也有彼此互相競逐之感,舉例來說,拔雅林庄的孤棧在運送過程中,不比其他庄頭以橫躺的方式運送,而以直立的方式運送,十分威風,因此拔雅林庄所製的孤棧又稱「風神棧」,總能引起眾人目光;福成庄的孤棧則因運送時全庄以跑步方式進入搶孤會場,好似王爺乘轎,故又被稱作「王爺棧」,頗有互別苗頭之意味。
第二次世界大戰起至民國八十年之間,長達半世紀的衰弱期,直接緊縮了頭城搶孤的社會連結,除了少數曾目睹(但未參與)的當地耆老外,幾乎沒有任何搶孤的痕跡留存於社會文化之中,然而,與搶孤同為中元普渡重要儀式「水陸法會」的主辦單位「中元祭典委員會」繼續承襲了頭城搶孤原有的社會網絡,使得宜蘭縣在倡議復辦頭城搶孤時,比預期的更加順利,在克服了技術問題後,基本上搶孤的社會網絡可直接自水陸法會的籌備組織體系中延伸,因此復辦後的搶孤籌備事宜,均由中元祭典委員會統籌辦理。
頭城搶孤進入民俗期後,由中元祭典委員會總理,並在民國八十三、八十四年因經費問題再度停辦兩年後,於民國八十五年時配合開蘭兩百週年紀念系列活動,訂定頭城搶孤的各項規則,如孤棧規格、參賽人數、賽制等,並開放年滿二十歲的健康男性組隊參加,而且外籍人士也具備報名資格(惟須由僱用公司統一組隊)[19],頭城搶孤踏出第二次擴張社會互動區域的步伐。藉由制度的完善、開蘭兩百年活動的宣傳等因素,頭城搶孤的民俗競技活動被大肆渲染至全台各地,此後每年的頭城搶孤,均有來自台北縣、屏東縣的隊伍參賽,而宜蘭縣境內的冬山鄉、羅東鎮也常有隊伍參賽,以民國九十八年的搶孤活動來說,報名之十二隊以宜蘭縣保留名額六隊、衛冕隊一隊,剩餘開放外縣市、外國隊伍參賽。因此,頭城搶孤變成了一個社會網絡遍及全台灣,甚至觸角向國際伸展的活動。近年來,更利用攝影比賽、煙火秀、園遊會等手法吸引台灣各地慕名而來的遊客,整體而言,頭城搶孤在近年來已經從「地方民俗活動」進而轉變成為「台灣民俗活動」。
從地方擴張至全台灣,還有一不可忽略的因素,即經費問題。頭城搶孤在民俗期的擴張與否,和經費是否有著落息息相關。民國八十五年舉辦頭城搶孤之祭典委員會主委指出:搶孤活動經費籌措困難,希望政府能將搶孤列入重點民俗慶典之一,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民間協辦,期望發展成為國際盛會[20]。此一擴張進程尚未完結,目前的頭城搶孤主辦單位仍以宜蘭縣政府為首,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擔任指導單位並補助經費,至目前為止,國際參與的狀況並不多見,仍以台灣島內為主要的參與對象。
搶孤活動從門口搶孤的「家戶形式」,逐步擴張至集體搶孤的「庄頭形式」、選手搶孤的「跨庄形式」,至民俗期則再擴張為「全台活動」,倘若不論搶孤於衰弱期的空間萎縮,則頭城搶孤的社會空間網絡為不斷擴張的形式。(圖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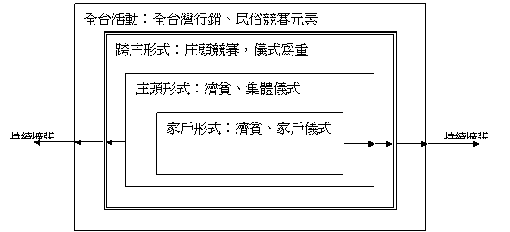 |
伍、走出地方與回到在地-頭城搶孤的將來
一、互動網域變遷所形成的困境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觀念下,頭城搶孤若要維持其盛況,便必須為了「開源」一事大費周章。在儀式期,搶孤的舉行為各庄重要之儀式,於鬼厲信仰無形的控制下,各庄認為應使孤棧高大雄偉、祭品豐富而多樣,否則鬼神將可能於來年降災,迫於鬼神之力而非舉行不可,因而可長久流傳;然而在衰弱期後,搶孤的儀式性格轉淡,鬼厲信仰控制社會的能力大幅削弱,尤其在政府、地方人士的刻意停辦下,搶孤的神話色彩早已褪去,半世紀後復辦之時不再以各庄的居民為主力,而由政府主辦,限於經費困窘,於是不可避免的須與商業掛鉤,諸如園遊會、廠商贊助等都是重要的經費來源,此外,為了使贊助商增加曝光率,也在搶孤進行前增添了許多大眾所喜愛的元素,諸如地方團體表演、煙火秀等,並結合攝影比賽期望使曝光率能達到最高。
頭城搶孤在此種資本主義式的經營下,有幾個現象可供觀察:其一,各庄間的面子之爭逐漸檯面化,由於各庄除負責製作孤棧外,由於參賽選手首重順風旗的取得,因此供品的種類減少、單一化,而將經費轉移至和順風旗一併取得的獎金,獎金的多寡將決定選手攀登的先後,因此形成各庄頭間的面子之爭,以民國九十八年的搶孤活動為例,搶得拔雅里風神棧順風旗的隊伍,將可獲得拔雅里所提供的二十萬元獎金,為歷來新高;其二,競賽的公平性已經超過儀式本身的代表意義,從前攀上孤棚後將供品灑下,由饑貧者取用的功能已成為徒具形式,今日的搶孤為避免觀眾影響比賽的公平性與安全性,因此除報名參賽選手與裁判外無人可接近孤棚,灑下的供品也因成本關係改為金紙。
上述二現象均代表著,搶孤儀式的內涵正不斷快速流失中,而以成本、利潤的計算為要項的資本社會正將頭城搶孤推向商業化,且在商業化的同時,為了拓展能見度以吸引贊助,遂加入更多不同元素而導致開銷更高,形成一正回饋的機制,因此若要以資本社會的觀點,讓頭城搶孤能永遠發展下去。其能見度擴展的最終極限,便是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讓此一原本與社會互動僅限於家戶門口或庄頭的儀式,擴展其互動範圍至全球尺度,可能如巴西的嘉年華(Carnival)一般,成為全球注目的重要民俗慶典。
二、回到在地的契機
今日大眾注目頭城搶孤的華麗煙火秀、聲光效果以及競賽過程的光鮮亮麗之時,卻有著文化內涵逐漸流失的隱憂,搶孤儀式在儒家的思想下的濟貧、佛道思想下的慎終追遠,甚至漢族先人開蘭披荊斬棘的辛苦歷程等文化意涵,在長達半世紀的衰弱期,以及後來擁有豐厚獎金、競爭激烈的搶孤競賽中,已逐漸被忽略或遺忘,長此以往,頭城搶孤將可能變成徒有形式,卻內涵空乏的民俗競賽。值得慶幸的是,主要籌辦頭城搶孤的中元祭典委員會承襲整套中元普渡的思考模式,並將之引入現代頭城搶孤的過程中,例如會場主持人於空閒時間解說頭城搶孤的社會意涵、歷史發展脈絡等,以及送鬼王、水陸法會等儀式的結合,使得今日我們仍能一定程度的窺探搶孤背後所隱含的意義。
走出地方之後,隨之而來的另一個收穫,則是短期地方收入的增加。隨著頭城搶孤的在大眾傳播媒體的能見度越來越高,加上地點從原來的佛祖廟廟埕改至烏石港北堤空地,腹地增大,遂吸引了各地遊客前來體驗,也因此,頭城搶孤再度成為庄頭民眾重視的議題,雖然與原本的社會意義大相逕庭,但頭城搶孤的續辦以及推廣,也逐步在地方民眾心中再度建立共識。
民國九十四年〈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布實施後,除有形的文化資產外,針對無形文化資產如儀式、禮俗等也逐漸重視,民國九十八年宜蘭縣政府計畫將頭城搶孤申請成為「國家無形文化資產」,並於蘭陽技術學院舉辦「2009年頭城搶孤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除國內的民俗文化、宗教學者外,也包括北京社會科學院和英國劍橋大學的學者也與會提供意見,展現宜蘭縣政府積極主導,希望能將頭城搶孤擴展成為國家級文化,以達永續發展的最終目的。
三、出與入-綜觀頭城搶孤的將來
搶孤在頭城的發展,從兩百餘年前的門口搶孤,歷經集體搶孤、選手搶孤等儀式期的階段,將濟貧、祭厲、慎終追遠等漢人傳統習俗發展成為一套完整的宗教儀式,並伴隨著社會的需求如安全、經濟等,逐漸擴大搶孤的社會互動領域,從家戶至各庄之間的聯合祭祀;後因戰亂、政治等因素導致頭城搶孤此類「勞民傷財」、「迷信」之舉予以廢止,遂進入了搶孤的衰弱期;半世紀後,由於地方政府的積極支持,頭城搶孤再度復辦,但受長期停辦之影響,人才凋零、技術失落,搶孤活動嚴肅的宗教的意涵被各家好手間的競爭、高額獎金與華麗的秀場表演所掩蓋,加上部分學者倡議消除搶孤的「迷信成分」,因此搶孤的發展逐漸走向純粹的競技、活動,而成為今日所見的「民俗期」,並靠著贊助、政府補助等維持經費來源。
在現今社會中,要使搶孤由民俗期重返儀式期的性質,實際上已不大可能,頭城搶孤所涵蓋的各街庄社經狀況,與儀式期的街庄民眾大不相同,因此,頭城搶孤要靠地方民眾自力舉辦的可能性已幾乎不存在,而地方政府經費著實有限,因此未來頭城搶孤可倚靠的最大經濟來源應為廠商贊助,故頭城搶孤的能見度越高、在臺灣各地知名度越高,對贊助廠商也越有利,也就能吸引更多廠商的贊助支援;在此種循環之下,頭城搶孤的社會互動領域已經大幅度的擴張。
搶孤活動社會領域的大幅擴張,對於頭城搶孤的永續發展有其正面助益,但也因必須迎合更多非在地人的需求,活動過程中純屬於頭城地區的文化內涵所占比例日漸縮小,作為一地方文化的代表,有內涵流失的危機存在。主辦頭城搶孤的中元祭典委員會也了解此一情況,因此配合活動現場進行儀式解說、網頁設置等方式,讓大眾能更清楚了解搶孤之內涵。
綜合上述,搶孤的持續發展必須倚靠社會互動網絡的擴張,提升其能見度,才有辦法維持最重要的經濟來源,然而,在迎合外地遊客口味之餘,主辦單位若能設法讓遊客更加了解,或親身體驗當年舉辦搶孤的社會背景、涵蓋的歷史、社會意涵以及因為進行搶孤而產生的社會網絡、工藝等,不需因「迷信」的理由而排斥其原有的宗教意義,將可使每年的搶孤不再只是衝著高額的獎金(包括攝影比賽的獎金)或純粹湊熱鬧,而更可以親身體會當年搶孤盛大、莊重的氛圍,如此一來,作為宜蘭縣申請國家無形文化資產重點的頭城搶孤,才不會淪為一個空有華麗外表,卻無實際內涵的競賽活動,已達到永續發展的終極目標。
陸、參考文獻
一、 書面資料
1. 片岡巖著,陳金田、馮作民譯(1981),《臺灣風俗誌》,大立臺版。
2. 吳明遠(2001),《中國五、六世紀盂蘭盆會之探源》,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3. 李榮春(1979),〈看搶孤〉,《蘭陽》,第18期,蘭陽雜誌社。
4. 林正芳纂修(2002),《續修頭城鎮志》,〈開闢篇〉,宜蘭縣頭城鎮公所。
5. 林正芳纂修(2002),《續修頭城鎮志》,〈搶孤篇〉,宜蘭縣頭城鎮公所。
6. 馬偕‧喬治著,林耀南譯(1959),《臺灣遙寄》,臺灣省文獻會。
7. 莊英章、吳文星纂修(1985),《頭城鎮誌》,宜蘭縣頭城鎮公所。
8. 陳志謙(1976),〈頭圍搶孤〉,《蘭陽》第7期,蘭陽雜誌社。
9. 游謙(1995),〈頭城搶孤的歷史與演變〉,《寺廟與民間文化研討會論文集》,漢學研究中心。
10. 黃進仕(2000),《臺灣民間「普渡」儀式研究》,南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1. 鈴木清一郎,馮作民譯(1989),《臺灣舊慣習俗信仰》,眾文圖書公司。
12. 劉昭吟(1994),《從祭典到觀光:頭城搶孤中的社區菁英、民俗信仰與觀光規劃》,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13. 蔡金樹(2007),《臺灣恆春搶孤豎孤棚活動發展之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14. 瞿海源(1992),〈恢復舉辦搶孤的探討〉,《頭城搶孤座談會會議手冊》。
二、 網路資料
1. 靜宜大學中文系台灣民俗文化研究室網頁(2009年11月28日):http://web.pu.edu.tw/~folktw/folklore/folklore_b11.htm
[1] 本文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社會學習領域概論課程期末個人研究報告。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九九級學生。
[3] 林正芳纂修(2002),《續修頭城鎮志》,〈開闢篇〉,宜蘭縣頭城鎮公所。
[4] 同上。
[5] 黃進仕(2000),《臺灣民間「普渡」儀式研究》,南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6] 吳明遠(2001),《中國五、六世紀盂蘭盆會之探源》,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7] 靜宜大學中文系台灣民俗文化研究室網頁(2009年11月28日):http://web.pu.edu.tw/~folktw/folklore/folklore_b11.htm
[8] 黃進仕(2000),《臺灣民間「普渡」儀式研究》,南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9] 游謙(1995),〈頭城搶孤的歷史與演變〉,《寺廟與民間文化研討會論文集》,漢學研究中心。
[10] 莊英章、吳文星纂修(1985),《頭城鎮誌》,宜蘭縣頭城鎮公所。
[11] 摘錄自林耀南(1959)翻譯之《臺灣遙寄》;原出處為Mackay G..L. ,1895, “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
[12] 片岡巖,陳金田、馮作民譯(1981),《臺灣風俗誌》,大立臺版。
[13] 鈴木清一郎,馮作民譯(1989),《臺灣舊慣習俗信仰》,眾文圖書公司。
[14] 林正芳纂修(2002),《續修頭城鎮志》,〈搶孤篇〉,宜蘭縣頭城鎮公所。
[15] 游謙(1995),〈頭城搶孤的歷史與演變〉,《寺廟與民間文化研討會論文集》,漢學研究中心。
[16] 李榮春(1979),〈看搶孤〉,《蘭陽》,第18期,蘭陽雜誌社。
[17] 林正芳纂修(2002),《續修頭城鎮志》,〈搶孤篇〉,宜蘭縣頭城鎮公所。
[18] 瞿海源(1992),〈恢復舉辦搶孤的探討〉,《頭城搶孤座談會會議手冊》。
[19] 林正芳纂修(2002),《續修頭城鎮志》,〈搶孤篇〉,宜蘭縣頭城鎮公所。
[20] 同上。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謝絕推銷、商業行為、情色與謾罵字眼,違者將逕行刪除留言。